首頁>要聞>沸點(diǎn) 沸點(diǎn)
被城鎮(zhèn)化落下的老人 被迫自我適應(yīng) “老農(nóng)”變“小工”
失去土地的羅家窯人依然平靜地生活著,他們尋找各種各樣的出路,有的打工,有的做生意,有的成了包工頭,有的已經(jīng)當(dāng)上老板。費(fèi)孝通曾說:“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土是他們的命根。”如今,或許只有老年人才能真正體會這句話所包含的愛與不舍了。
羅家窯,湖北省黃岡市團(tuán)風(fēng)縣的一個城中村,一個典型的中部地區(qū)貧困縣村莊,記者今年在這里蹲點(diǎn)調(diào)研時(shí),它仍在經(jīng)歷浩浩蕩蕩席卷而來的城鎮(zhèn)化大潮。時(shí)代潮流不可阻擋,只是,一些老年人悄悄地被落下了。
“要是地沒了,真不知道怎么辦了”
羅家窯村很特殊,因?yàn)樗且粋€移民村。1958年之前,這里是一片沼澤,荒草叢生,了無人煙。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周邊幾個公社的青壯年勞動力,以及一座小型水庫的庫區(qū)移民,陸續(xù)遷到這里,圍墾造田、開荒種地,逐漸成了一個區(qū)屬農(nóng)場。1983年分田到戶,農(nóng)場改名羅家窯村。作為一個移民村,羅家窯少了一些宗族紐帶和親緣關(guān)系的牽連。村里800多戶人家2300多人,有100多個姓。
現(xiàn)在,它又成了一個典型的城中村。羅家窯位于團(tuán)風(fēng)鎮(zhèn),1996年團(tuán)風(fēng)設(shè)縣,團(tuán)風(fēng)鎮(zhèn)變成了縣城,羅家窯村成了縣城擴(kuò)張的主要土地來源。村里原有土地登記面積783畝,但實(shí)際上,為了逃避稅費(fèi),土地瞞報(bào)的比較多,實(shí)有1000多畝。經(jīng)過幾輪“蠶食”,這些土地已全部被征用,目前還有300畝左右沒有退出。
在這僅剩的300畝土地上,有一棟很破舊的紅磚瓦房孤立中央,特別顯眼,四周都是棉花蔬菜之類的農(nóng)作物,再外面就是村里一排排樓房和縣城的高層小區(qū)。
我們先后三次來到這座房子,69歲的屋主人夏傳杰都是頭頂草帽,在屋旁的地里勞作。“這塊地前年就被征走了。只要一天沒有強(qiáng)行不讓種,我就種一天。種了一輩子的地,馬上就沒有地種了,以后生活怎么辦?”夏傳杰是1963年遷到羅家窯村的,那時(shí)只有17歲,在這片“草比人高”的沼澤上開荒拓土,成為羅家窯村最早的定居者之一。
夏傳杰的兩個兒子生活都很困難,“混得不好”,老兩口沒有指望讓兒子們贍養(yǎng)。像村里很多老人一樣,他們獨(dú)立生活,2005年的時(shí)候,找村里借了錢,在自家耕地里搭建了這所磚瓦房,將20多年前建的老房子讓給兩個兒子住。
夏傳杰種地經(jīng)驗(yàn)豐富,除了種植棉花、玉米、油菜之外,還種有3畝多蔬菜,一年下來,幾畝地的收入有1萬元左右,這是他和老伴主要的生活來源。“去年我的腳被機(jī)器打了,腳筋斷了還沒接上,老伴中風(fēng),種地也種不動了,過一天混一天吧!要是地沒了,真不知道怎么辦了。”夏傳杰說。
被迫自我適應(yīng),“老農(nóng)”變“小工”
當(dāng)耕地變成一條條馬路,建起一幢幢高樓,和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人受到的影響最大。在羅家窯村,像夏傳杰這樣還能堅(jiān)持種地的老人也不多了。62歲的徐金庭自己沒有地,租種了村支書童建文家的幾畝地。國慶節(jié)過后的10月10日,他拖著被風(fēng)濕病折磨得行走艱難的雙腿,在地里十分緩慢地刨坑、埋肥、撒油菜種子,一直忙到下午一點(diǎn)鐘,才收拾東西回家做飯吃。
“種油菜、棉花省事一些,要是種菜,還要挑水澆灌,你看我這樣子哪挑得了。”老徐告訴記者,自己以前一直在外面打工,現(xiàn)在打不動了,沒辦法才回家種地,一年只能搞2000多塊錢,去年種棉花,賣了4000多塊錢,本就要3000塊,種一年地不如做一個月小工。
當(dāng)然,羅家窯村老人面臨的更主要問題還是無地可種。許多老年人被迫適應(yīng)這種狀況,“老農(nóng)”變“小工”,實(shí)現(xiàn)由“耕”到“工”的艱難轉(zhuǎn)變。
75歲的汪榮清曾經(jīng)是大集體時(shí)期的村干部。今年春節(jié)前記者采訪他的時(shí)候,頭發(fā)花白的老人剛從建筑工地“做小工”回來。“我18歲來這里開荒,到處是雜草,開墾了幾十年,沒想到人老了,土地沒有了。”他一臉無奈地對記者說。
汪榮清50歲的兒子在深圳當(dāng)廚師,兒媳婦也在那里,為了春節(jié)期間的兩三倍加班工資,夫妻二人十幾年沒有在家過年了。
“土地被征了,只有幾萬元的補(bǔ)償,這些錢兒子做房子用了。我和老伴現(xiàn)在每人每月有國家的養(yǎng)老金55元,村里發(fā)的失地補(bǔ)償金85元。老伴生病后,這些錢根本不夠用,地也沒有了,只有出去做小工,挑沙子,拎灰桶,一年能掙3000多塊。”
和汪榮清一樣,羅家窯村的老年人失去土地后,很少由子女養(yǎng)老,只要能勞動,就會想辦法打零工掙點(diǎn)生活費(fèi)。67歲的江蓮英,兩個兒子快30歲了,還沒有找到對象,老伴風(fēng)濕病,喪失勞動能力,她在外打兩份零工。今年春節(jié)前直到臘月二十八,她仍在工地給別人打掃衛(wèi)生。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不再強(qiáng)壯,打零工的事情已經(jīng)不好找了。汪榮清說,別人不愿請,怕出問題,一般零工170塊一天,六七十歲的老人最多120塊。
20年來,羅家窯村從純農(nóng)業(yè)村莊變?yōu)槌侵写澹ネ恋氐霓r(nóng)民,面對徐徐駛來的城鎮(zhèn)化列車,或者搭上了,或在追趕中,或在站臺上觀望,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的選擇,命運(yùn)因此而改變。在近20年的征地歷程中,許多人也漸漸褪去了失去土地的不適感,調(diào)整自己的心態(tài),融入城市生活。當(dāng)然,這不包括那些為數(shù)不少的老年人。
城鎮(zhèn)化中,老年人失去最多得到最少
在村干部的幫助下,記者對羅家窯村村民的生活狀況作了一個粗略的統(tǒng)計(jì)。全村外出打工從事建筑行業(yè)的人最多,泥瓦工、木工、涂料工、裝潢工接近100人;從事汽車運(yùn)輸、機(jī)械作業(yè)的將近50人;在附近賓館、超市、餐飲行業(yè)打工的有50人左右;打零工的有六七十人。
“打工經(jīng)濟(jì)”在羅家窯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結(jié)局。用一些村民的話說:“有點(diǎn)能力的,搞一搞都富起來了。”
現(xiàn)任村支書童建文就是羅家窯村成功者的代表。在許多村民的記憶中,童建文家曾經(jīng)是羅家窯最貧窮的家庭之一,但現(xiàn)在他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攪拌站,各種機(jī)械設(shè)備加起來價(jià)值幾千萬元,是全村最富的人之一。
1995年,28歲的童建文到省城武漢打工,給別人開車,混得最差的時(shí)候,連坐公交的錢都沒有,不得不每天步行幾公里去攬工。一個偶然的機(jī)會,他找到開工程車的活,23天賺了2000多塊錢。他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賺錢的好行當(dāng)。憑著精明能干,童建文在工地學(xué)會了很多工程知識,從此走上了靠工程施工發(fā)家致富的道路。
在羅家窯村,每一位童建文這樣的“鄉(xiāng)村精英”都有一段艱苦奮斗的故事:程桂林夜晚到田里捉小動物,見過滿溝的蛇“在開會”;夏和平7000塊錢起步開小賣部,曾被大雪壓塌,無處安身。但后來,他們都通過承接各類工程項(xiàng)目“先富起來”,抓住了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城鄉(xiāng)建設(shè)投入迅猛的時(shí)代機(jī)遇。
但并不是所有的奮斗者都能成為幸運(yùn)兒。詹靜文的家是一幢破舊的兩層樓房,可以看出,這是一幢曾經(jīng)代表了家庭實(shí)力的房子,只是隨著歲月的流逝,一直沒有整修而顯得斑駁破舊。詹靜文告訴記者,房子是1987年修建的,那時(shí)候他開貨車跑運(yùn)輸,日子過得還不錯。但后來,整個家庭的命運(yùn)因?yàn)閮鹤拥摹肮植 卑l(fā)生了逆轉(zhuǎn)。
兒子詹紅生已經(jīng)39歲了,患有先天性“肝豆?fàn)詈俗冃浴奔膊。_不能久站,手不能伸直,手指彎曲,不停顫抖,碗筷也端不穩(wěn)。從12歲發(fā)病到現(xiàn)在,一直靠藥物控制病情。“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能掙到兒子的藥費(fèi)錢。”年近七旬的詹靜文仍然每天到建筑工地做小工,他最擔(dān)心的是自己不能動了,兒子誰來照顧。
失去土地的羅家窯村,已經(jīng)形成“紡錘形”的村莊結(jié)構(gòu)。“紡錘”的一端,是村里的“精英層”“富裕層”;“紡錘”的另一端,是相對困難的“低收入層”和“貧困層”;中間占大多數(shù)的是“打工層”。對老年人而言,連最常見的“打工經(jīng)濟(jì)”,也與他們漸行漸遠(yuǎn)。在城鎮(zhèn)化中,羅家窯的老人們失去了最珍視的土地,卻沒有享受到市民的社會保障。
采訪中,不少老人懷念起從前農(nóng)場式的紅磚瓦房時(shí)代,一排排整齊劃一,鄰里間雞犬相聞。但是,他們知道:回不去了。“土地沒有了,房子變了,生活也變了!城鎮(zhèn)化已經(jīng)是不可逆轉(zhuǎn)的趨勢。”村民孫楚炎說。(記者 梁相斌 皮曙初 余國慶)
編輯:鞏盼東
關(guān)鍵詞:被城鎮(zhèn)化落下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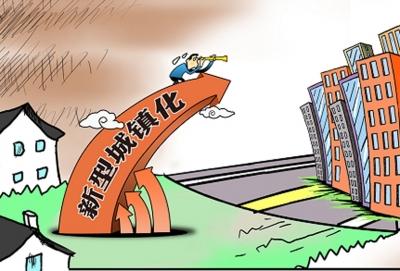


 “超級月亮”現(xiàn)身堪培拉
“超級月亮”現(xiàn)身堪培拉 特朗普發(fā)表其執(zhí)政以來的首次國情咨文演講
特朗普發(fā)表其執(zhí)政以來的首次國情咨文演講 保障春運(yùn)
保障春運(yùn) “歡樂春節(jié)”挪威首演閃耀北極光藝術(shù)節(jié)
“歡樂春節(jié)”挪威首演閃耀北極光藝術(shù)節(jié) 靚麗海冰
靚麗海冰 春運(yùn)路上有了“列車醫(yī)生”
春運(yùn)路上有了“列車醫(yī)生” 阿富汗官員:應(yīng)抓住機(jī)遇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shè)
阿富汗官員:應(yīng)抓住機(jī)遇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shè)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到訪武漢大學(xué)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到訪武漢大學(xué)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xué)明
錢學(xué)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jìn)
許進(jìn)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guān)牧村
關(guān)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wèi)
謝衛(wèi)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xué)誠法師
學(xué)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